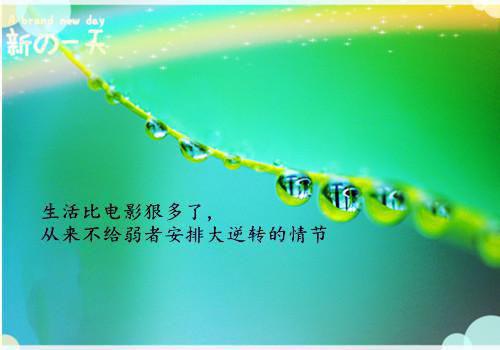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作品的排名一向是很难的,因为鉴赏能力的差别和个人主观爱好的不同,往往很难对文学作品排出来一个服众的排名。
文学有奖,自古已然。作家获奖,名次虽分先后,高下立见,但孰优孰劣,未必就此定论,也是自古已然。文学评奖,很难做到公平公正,作家拿奖,未必能够孚洽众望,那就更是自古已然。故而世人皆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其实了了者,名单可开一大串;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竟然未获者,名单更是一大串。但是,诺奖所以闻名遐迩,其奖金之高,很让一些人眼红不已,因而垂涎三尺。
中国的元朝至正年间,曾经搞过一次文学奖,其实是一次诗歌大奖赛,其奖金堪与诺奖媲美。
那时,虽近元末,尚未天下大乱,东南沿海,物阜民丰,江南一带,富甲天下。即使后来张士诚割据吴中,自称诚王,政权相对稳定,统治也相对宽松。张虽贩私盐出身,却是一个文学老青年。热衷笔墨,雅爱词章,很喜欢扎在文人堆里,箕坐饮酒,唱和啸歌。他在苏州设弘文馆,开集贤馆,高楼雅座,延揽文士,管吃管喝,善待礼遇。故而苏、松、淮、扬地区的诗社活动,经此提倡,风起云涌,煞是景气。
张士诚还专程征聘元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他的咨议参军,主持文事。元之行省,就是行中书省,等于是中央派出单位;而参政,官至二品,在地方上是拥有相当权威的人物。饶介官大,远不如他文坛领袖的名声大。饶介(1300-1367),江西临川人,字介之,自号醉樵。元末诗人,书法家,据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称,“释道衍曰:‘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陈惟演、惟允、杨孟载诸辈,皆与交。’衍亦与焉。”时人评他:“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褒其诗曰:“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誉其字曰:“飘逸畅朗,清丽流放,神追大令(王献之)。”张士诚入吴以后,饶介杜门不出,这就是文人的清高了。可这样一位知名度高,号召力大,追随者众,影响面广的文学大人物,贩私盐的张士诚肯定早有所闻,立马拎了两瓶好酒,封了一份厚礼,亲自登门,请他出山。

饶介谦虚:一介微士,是做不来什么事的。
与那个视文人为敌的朱元璋不同,张士诚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只要先生大驾光临,就令吴门蓬荜生辉了。
据说,他加入张士诚政权以后,“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在此期间,他周围聚集了如高启、王彝、杨基、张简、徐贲、张羽……后来在文学史上称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一大批诗人,因为声气相投,因为同道契合,饶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文学大奖赛。大江南北,报名响应,应征作品,纷至沓来,成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张士诚是个好热闹的人,最怕冷冷清清,饶介是个大气派的人,最怕抠抠吮吮,于是,政府出钱,咨议出面,官员染指,文人插手。诗这个东西,说到底,不过“神马浮云”,但钱这个东西,却不是水中之月,那些日子里的苏州城,成为诗的世界,也成为钱的世界。任何评奖的最后,都是和实际利益挂钩的。
连后来官修的《明史》,都记载了这次的元朝文学奖。“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现在已弄不清楚评奖当时的情况,有无猫腻,是否红包,但一等奖的奖金,与二等奖的奖金,其相差之悬殊,令人匪夷所思。元、明时的市制一斤,约合公制600克,虽同为一饼,各重三斤,为1800克。按照近日菜市口百货商店的黄金饰品柜台售价,黄金一克,价358元,白银一克,价8元。这就是说张简的一等奖,为人民币64.44万元;稍高于本届茅盾奖的50万元,稍逊于每年涨价的诺奖100万元。而高启的二等奖,则是笑话了,仅合人民币约14400元。64万比1万,要是放在当下网络环境里,不知该有多少网民奋起“拍砖”?
张简的《醉樵歌》,当然写得也是气势磅礴,但读得出来,这是一首为手不释杯的饶介量身定做的诗,或许是他得于高置榜首的原因吧?但中国人都知道,在明代文学史上,得二等奖的高启,才是大明王朝第一流诗人。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认为高启为明初最杰出的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高启为明初“吴诗派”的开山鼻祖。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高度评价高启:“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因此,一过性的文学奖,其时效意义对文学本质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浪花泡沫,看似喧嚣,很快也就随风而逝。至于文学的优劣,至于作家的高低,只有时间,而且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