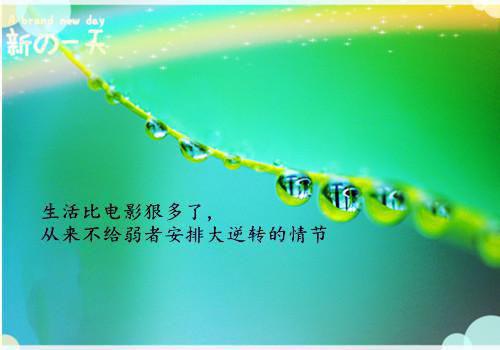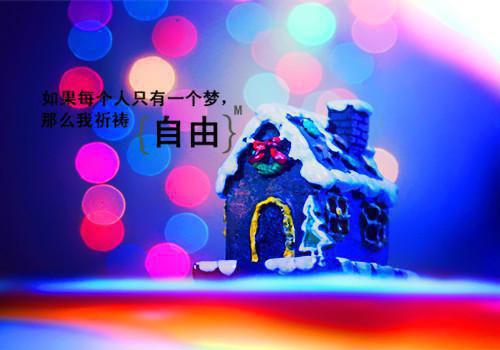最近“精日”上蹿下跳引起众怒,再加上妇女节刚刚过去,所以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个让“精日”脸疼的女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拉贝日记》,发现这一重要史料的人叫张纯如。其实,除了《拉贝日记》,张纯如还发现了《魏特琳日记》!

但是,知道张纯如和知道拉贝的人,远远比知道魏特琳的人多得多。
当年,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年,日寇疯狂屠城,她却五次拒绝撤离,执意留下来保护难民,撑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岛,化身“活菩萨”给了多少中国人活下去的希望。
甚至,可以说,她为中国燃尽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文章有一点点长,让我们一起耐心认真聆听她的故事。
一、她不是洋鬼子,她是“华小姐”
1886年9月27日,魏特琳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西科尔小镇的一个铁匠家庭。
因为家境贫穷,她在学生时代打过不少零工挣学费。1912年,魏特琳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士学位,尽管半工半读,毕业时还是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毕业那一年,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当她听说中国的教育不发达,不顾亲友的反对,执意来到了中国。
根据姓氏Vautrin的音译,魏特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华群”,学生亲切地称呼为“华小姐”。
第一站是在合肥,她排除万难建立了女校;第二站是在南京,她在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以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课程,培养女中的教师、行政管理人才。
此外,她还想尽办法募捐,在金大附近买地盖教室,专门招收附近的贫困孩子,鼓励金大的女学生担任教师,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
虽然魏特琳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她对中国这片热土怀有神圣的使命感,甚至因为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放弃了在美国等她结婚的男朋友,从此孑然一身。
时至今日,魏特琳的雕像依然坐落在她曾出任代理校长的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
在她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
可以说,她的到来,给中国的女子教育,穷人教育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包抄,大战将至!
17日,宋美龄在撤离前,派人把自己的钢琴搬来,赠给了金陵女大。魏特琳知道危险即将来临,在12月1日劝离了校长吴贻芳、,却留下了自己,当时陪她的还有十几名中国老师。
事实上,魏特琳所在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些外国人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并不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它对主权国家并不具约束力。魏特琳心里很明白,作为中立国公民,她留在沦陷后的南京也并不是绝对安全。
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的回答则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并毅然在“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事实上,这已经是魏特琳第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了。
在第2次接到通知后,她就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
“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就这样,魏特琳不仅留了下来,冒死建议一旦日军攻入南京,要能仿效上海,在金陵女院建立起难民救助所。
这个建议,日后成了她沉重的负担,甚至因此得了重病。
三、“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几乎同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整个南京城火光漫天。
日军进城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日军还是展开所谓“大搜查”。许多日兵进入民宅搜查,见到女人或是就地强奸,或是拉回部队配给士兵轮奸。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的那样: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魏特琳仍然在救济妇女儿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了难民所。而且,用她的手中的笔,记录下了日寇的暴行。
“(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在学院中树立的中立区标志,和日本大使馆官员写的不许日本兵进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只有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
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现,拔腿便跑,但有时也用武器威胁她,甚至动手打她。
这些事情,在中国守军营长郭歧的《陷都血泪录》中有记录——魏特琳,是他的救命恩人。
在难民所的日子里,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有一次,她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她们大多一无所有,魏特琳要向这些难民提供吃住,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压力顿时增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而且,她不知道这种压力还要持续多久。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她不仅保护女性,还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
魏特琳一直想方设法改善难民的生存环境,她请来外国医生为难民看病、打预防针,为儿童弄来奶粉和鱼肝油,为女难民开办学校,补习文化知识……难民们叫她“活菩萨”、“观音菩萨”。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人,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国人。她曾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
“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太阳旗的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你永远不要忘记!”
这段时期,魏特琳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真实记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和个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创伤,更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
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劝说下,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国治病。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回国仅一年,用自杀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