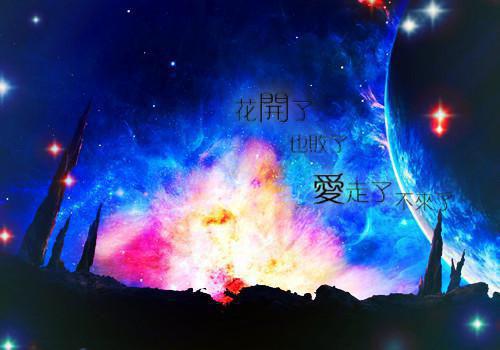一、借鸡生蛋的隐患
626年冬,东突厥汗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天灾,牛羊多死,食粮紧张,部族间的矛盾大幅加剧,薛延陀等数个强大部落趁机群反而出,东突厥汗廷三度出兵镇压,结果连遭惨败,本就剩余不多的实力再遭重创,曾经称霸漠北的强大汗国一时间变得虚弱不堪。唐廷见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急急出兵夹击,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东突厥的部众和土地,曾经雄踞北亚的东突厥汗国灭亡。
646年,薛延陀汗国中的回纥部造反,与薛延陀部争夺统治族地位,薛延陀陷入大规模的分裂内乱之中。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回纥人轻易便击杀了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灭亡。就在回纥人即将接管薛延陀的地盘和部族,乘势崛起之时,大唐及时介入,出动大军前去抢夺胜利果实。此时薛延陀汗国中的各部族正因国中大乱而陷入一盘散沙的困境,无力抗拒唐军,其中一些被迫依附了唐朝,另一些则投靠了旧同僚回纥。刚刚吞并了大量薛延陀残部的回纥急于整合内部,消化新获得的草场和部民,暂时不愿与唐朝为敌;加之游牧民族只重实利,不务虚名,遂带着麾下众部族向唐称藩,整个漠北都在名义上成为大唐的羁縻区。由于北塞已无强邻,唐帝国的北疆自此获得了三十余年的平静。
尽管漠北诸部大多向唐朝表示了口头上的臣服,但对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那些强大的部族,唐朝却无法真正掌控。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回纥的部族,更是有恃无恐,不将唐朝放在眼中,很多甚至还对唐朝怀有敌意,只是口头上并不撕破脸而已。当然,漠北也有一些部族与唐朝走得较近,其中一些甚至要靠大唐的庇护才能免于被其它部落所吞并,唐朝则对这些部落加以利用,以达成自己在草原的利益。在依附于唐朝的漠北部落中,当年被薛延陀颠覆的东突厥的残部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唐朝常常要求其出兵助战,充当自己对外扩张的马前卒。突厥铁骑是精锐之师,战斗力比唐军更高,只是因为人数较少,各部族间又缺乏凝聚力,相互牵制,才不得不奉唐号令,履行藩属国从征的义务。
对于唐朝而言,裹挟大量异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阵营,与汉军混编做战,在短期内可以说获得了颇佳的效果。在李世民推行府兵制之后,唐军士兵便由一群农民组成,出征前才临时集结,士卒缺乏训练,彼此间毫无配合,因此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可在与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的部族军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双方的优势互补,唐军的数量优势和唐帝国在财政、物资上的充足,与部族军的精锐勇悍、擅于骑射、以及强大的远程奔袭能力相结合,联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朝对外的扩张也因而一度比较顺利。

凭恃着较强的国力、财力和数量众多的人口,大唐迫使羁縻区中的众部族奉自己为盟主,再以宗主国的身份号令诸部族从征,将这些异族部落紧紧绑在自己对外扩张的战车之上。对于与唐合作,奉唐为军事同盟盟主一事,诸部族的态度并不相同。一些较为弱小的部落要依附唐朝才能自保生存,只好唯命是从;一些部族虽能自保,但畏惧大唐,只得违心奉命;一些部族实力较强,但内部不和,一盘散沙,虽然士卒精锐,却相互制衡,亦不敢与唐朝相抗;更有一些部落,虽然实力甚强,但其首领或被唐廷以高官厚爵拉拢,不愿冒险造反,或者干脆就是大唐扶持起来的傀儡,仅凭自身威望不足以掌控权力,只好选择与唐朝合作;一些部落则因长期胡、汉共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民形成了融合,无法独善其身……总而言之,为了达到裹挟诸部的目的,唐廷往往软硬兼施,对强大者诱之以利,弱小者迫之以武,再辅以收买部族首领、以互市交换出兵等手段,驱策其为己所用。
在新、旧《唐书》中,常能看到周边藩属、邻国随唐从征的记载,比如薛延陀在639年时就曾主动提出要配合唐军征伐高昌。647年时,王玄策仅以匹马入吐蕃,便拉出一支吐蕃兵和尼泊尔兵攻入印度,大掠而还。在史书中,通常将这些现象解读为大唐国势强盛,周边诸国心怀敬畏,有些主动献媚讨好,有些则是不敢不从,被迫出兵助攻,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中原史官们自高自大的一面之词。大唐在号召诸国、诸部从征时,以自身武力威慑强迫只是次要手段,大部分部族也根本不会卖唐朝的账,军事同盟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实际利益。
当对手实力较弱时,大唐以宗主国的身份纠集众藩属出兵,通过侵略战争进行领土扩张,并与诸藩属一道瓜分其国内的财帛和人丁,以赤裸裸的利益做为联接纽带,保障军事联盟的稳定性,其模式类似于原始人合作进行捕猎。对于这种能够捞取大量好处的机会,诸部族自然欣然从命,薛延陀主动请缨从征西域便是出于此心(李世民断然拒绝了夷男可汗的请战,也是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仅凭既有的力量,联军便足以攻取小小高昌,自然不愿意有人在西域分一杯羹,更担心薛延陀会通过此役而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进而壮大)。而王玄策之所以能够从屡次痛击大唐的敌国吐蕃那里借到兵,也不是因为什么吐蕃人要讨好唐朝,真实原因其实是吐蕃人也希望趁机攻掠印度,攫取人丁和财帛。最终蕃军和尼泊尔军掳夺了大批奴隶和财物回国,而进攻的主持者唐朝却只得到了印度人的憎恨,得失之间,其实颇为值得玩味。
既然大唐征发诸部的根本手段是以共同获取利益为饵,那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面对不同的进攻对象时,诸部的意愿常常大有不同。在出征富饶且利于骑兵奔袭的西域(如高昌、龟兹,或是西突厥分裂后的某个部落)时,诸藩属往往积极响应,甚至主动求战;可当出征的对象是贫瘠却又较为顽强的对手时,很多部族就不愿前往。638年时,吐蕃在攻入唐境,烧杀掳掠一番后,安然撤兵回国,李世民却无力报复,反倒不得不送出文成公主,借和亲的手段来加以怀柔,举措十分软弱,其原因之一就是仅靠汉军无力进攻对方,而吐蕃贫瘠、强悍、地形易守难攻,诸部族军多不愿从征,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武装打击。高句丽的情况与吐蕃差不多,做战顽强又贫瘠少财,路途遥远且天寒地冻,因此诸部都不愿前往,对铁勒诸部的强行征发还引发了大反叛,迫使唐军在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关键时候将北线军队撤回镇压,这也正是第二次征辽无功而返且损兵折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唐帝国在对辽东作战时,可倚赖的藩属就只有辽宁、吉林一带的靺鞨部族军了。
显而易见,大唐所采用的这种“借鸡生蛋”的军事合作模式并不稳定,存有极大的隐患。由于自身的战力不足,唐廷对部族军普遍缺乏威慑,无法自如控制,只能利用各部族间的矛盾加以挑拨分化,或诱之以利。然而以战斗力较弱却数量较多的军队,去控制少量异族精兵做战,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一时的对外胜利也只不过是稍瞬即逝的沙上楼阁、镜花水月。从本质上看,做为一群缺乏凝聚力的混合军队,在打顺风仗时,往往能在取胜后大肆劫掠的鼓舞下奋勇做战;但一遇到稍强的对手,战局陷入僵持甚至不利状态后,就会迅速土崩瓦解,争先逃窜。这是战争的规律,从古至今临时啸聚起来的流寇们莫不如此,以藩属军为主战力的唐朝联军自然也不能外。大唐从630至660三十年间趁着周边诸国内乱而大幅扩张,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频频惨败,丧师失地,而且常常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惨况,这些其实早就因唐军的这种做战模式而注定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初期的军事扩张皆仰赖对藩属军的成功利用,但这也恰恰成为唐朝之后对外扩张的桎梏。唐帝国有了可依赖的对象,自然就不思进取,不肯再花力气去发展自身汉军的实力,等到众藩属看清大唐的外强中干,自身又羽翼渐丰之后,便拒绝再替大唐卖命,唐帝国在遇到强敌时自然就不能抵挡,这也正是唐朝对高句丽的几次倾国远征都铩羽而归,之后又败于小小新罗之手,在660年之后更饱受吐蕃欺压的原因所在。
更致命的是,当握刀的手缺乏力度以后,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大唐由威风凛凛四面扩张,突然变得狼狈万分四处挨打,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全靠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投机取巧;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府兵制的逐渐崩解,唐朝自身本就平庸的军事力量进一步下降,而诸藩属则渐渐坐大,此消彼长之下,诸藩属渐渐脱离了控制。手中的刀非但不肯再为己所用,反倒砍向了自身,大唐陷入窘迫处境自然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二、国之将亡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唐军战力低弱,远非安禄山麾下胡兵对手,因此接连大败,叛军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李隆基以名将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洛阳抵御叛军。封常清急急拼凑了六万兵马,但比起安史叛军,这些人可谓名符其实的乌合之众,一交手便惨遭铁骑蹂躏,大败;退至葵园又战,大败;退至洛阳上东门再战,大败;叛军攻入东都,与唐军在都亭驿巷战,唐军大败,退守宣仁门;叛军乘胜进攻,唐军又大败。六场大败之后,封常清实在撑不住了,率残部向西落荒而逃。在此役中,唐军的表现极为不佳,堪称是一败如水,据《旧唐书-忠义传》记载:“及兵交之后,(唐军)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
叛军于755年十二月攻占洛阳,旋即便抵达京师屏障潼关,哥舒翰统二十万唐军出关相抗,结果大败亏输,唐军士卒尸横遍野,掉进黄河淹死的就有几万人,绝望的号哭声惊天动地,最终仅余八千,几乎全军尽没,燕军旋即轻取潼关,大唐名将哥舒翰投敌,安禄山乘胜兵进长安,刚刚惨败的唐军毫无阻挡之能,四散奔逃。眼见大势已去,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带着后宫佳丽和少数亲信重臣偷偷逃往成都。第二天早朝时,眼见龙椅上空空荡荡,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才明白,自己已经被敬爱的君王给抛弃了,于是也纷纷作鸟兽散,京城顿时大乱,五军崩解,秩序荡然无存,京城百姓冲入皇城,焚烧皇宫,劫掠财宝,甚至还有骑驴上殿者,大唐皇家的威严丧失殆尽,景象之凄惶,宛如末世。(“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旧唐书》卷115)
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策划了马嵬兵变,于756年七月在郭子仪等军头的拥立下强行继位,夺了老爹的皇位。不久后安庆绪杀父而代,燕军发生大规模内讧,史思明率半数兵马自立。本已胆寒的唐肃宗看到如此良机,精神大振,遂封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把握机会,乘隙大举反攻。郭子仪统唐军主力进击,虽然时机把握得不错,但由于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连内乱正酣,人心惶惶,已然四分五裂的叛军一部都打不过,结果惨败于兴平,士卒死伤枕籍,局面自此更为不利,郭子仪自请贬职三级,最后被降为左仆射。与此同时,大唐的经济命脉江淮地区的局势也同时恶化,之前全靠睢阳(今河南商丘)和南阳两座坚城挡住南下江淮的叛军,得以不让对方切断唐王朝的钱粮来源,但南阳在守了一年多后仍然等不到援军,城中“人相食”,“饿死者相枕藉”,于757年夏陷落,睢阳则于十月陷落。其它方向上,灵昌陷落,太守许叔冀败退彭城;陕郡被叛军攻陷;重镇上党虽然没丢,但守城的梁柱,大将程千里被叛军名将蔡希德俘虏……总而言之,此时的整体形势对唐廷极其不利,大唐已然濒临彻底崩盘的绝境。
三、乞兵回纥
此时长安已然沦陷数年,一个国家的首都是皇权最重要的象征,被逐出首都的唐廷本就颜面扫地,如果不能迅速平定叛乱,让威信进一步下滑,那一旦让各地的节度使们感到中央已然式微,产生趁机自立的念头,那大唐的统治很可能会在短期内彻底崩塌。眼见大唐已经走到了亡国边缘,唐军此时的实际统帅,名将郭子仪在确定大唐根本无力剿灭叛军之后,于八月劝说唐肃宗不惜代价乞兵于回纥汗国,借兵平叛。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换取回纥人出兵,唐肃宗许下了一份极高的报酬:“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换言之,在收复长安后,土地和老幼归大唐所有,而城中所有的财物(包括每个百姓家中的私产),都已经被唐廷出让给了回纥人,对方可以恣意劫掠,而城中所有的青年男女也要任由其掳掠回国为奴。
回纥既得重酬,欣然出兵,据《新唐书》卷246记载:“贼皆奚,素畏回纥,既合,惊且嚣。王分精兵与嗣业合击之,守忠等大败,引而东,通儒弃妻子奔陕郡。王师入长安”。《旧唐书-回纥传》则记载:“贼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回纥驰救之,匹马不归,因收西京。”由于叛军“素畏回纥”,见唐军中竟有回纥人襄助,本就心惊胆寒,加上针对唐军制订的战略部署被回纥人打乱,顿时惊慌失措,联军遂在长安城外大败安庆绪麾下叛军,收复长安。
757年十月十八日壬戊,联军不战而下洛阳。就在大唐军队进入洛阳的时候,那些苦于叛军骚扰,日夜企盼唐军到来的百姓们才惊诧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热爱的祖国所出卖。按照大唐与回纥人的协议,此次回纥军可以在以东都洛阳为圆心,半径两百里的区域内进行合法的奸淫掳掠,十余万唐军则对这些暴行视若不见,不闻不问。

那些后来信仰回教的穆斯林士兵们并没有放过这个掘地三尺的大好机会,他们怀着对汉人和大唐的鄙夷,在洛阳城中大掠三日。就在回纥人还“意犹未厌”之时,残存的洛阳“父老”们又敛集了罗锦一万匹送入回纥营中,回纥人的暴行这才渐渐停止。由于此次回纥人初入大唐,尚存与唐朝结好之意,因此在施暴时尚有节制,只是如约抢财物,掠青年男女,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洛阳城中的老迈婴幼大率无恙,被洗劫之后的洛阳也并未彻底残破,这与下一次回纥人再入东京时那惨绝人寰的灾难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四、五万叛军大破六十万唐军
在回纥人(唐军也起到了辅助作用)歼灭了安庆绪部叛军的十几万精锐部队后,大唐的军事压力剧减,而叛军则实力大损,况且叛军兵卒们得知回纥居然出兵援助大唐,无不裂胆,很多中间势力,甚至亲叛军的势力也开始向唐廷倾斜,大唐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了双重优势,形势大为改观。
然而此时回纥人已然归国,唐军集团重又陷入羸弱不堪的状态,叛军遂能够再次逞威。758年九月,郭子仪和契丹族名将李光弼统军二十余万围困安庆绪于邺城,之后唐军兵力又陆续增至六十万,然而此时的唐军都是些乌合之众,以十倍兵力围攻小小邺城四个多月竟不能克,表现异常太过拙劣。郭子仪最后连掘开漳水河堤,迫其改道灌城的办法都用上了,也不知道下游多少百姓因此妙策而遭灾破家,邺城最终水深数尺,又断了粮,唐军却仍不能克。一直拖到759年二月末,史思明统精兵五万援安庆绪,唐军步骑六十万列阵于邺城北部拒之,双方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野战。(“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津兵五万敌之”——《资治通鉴》)
唐军此次几乎拼凑了旗下的全部兵力,试图倚多为胜,抵消自己野战能力较差的劣势。然而绵羊再多也不是虎狼的对手,史思明率精骑突入唐军阵列,唐军损失甚大,很快便难以支撑。就在此时,大风突起,更加剧了唐军的溃败,九节度中实际的首领郭子仪(另一个威望与他齐名的是李光弼)见大势已去,便扔下友军,引本部不战而逃。郭子仪所部的朔方军是唐军中最精锐者,本为全军殿后坐镇,他这个主将率先统军溃逃,更是加速了全军崩塌的进程。正在前方激战的军卒见后军已去,立时毫无战志,整个唐军的阵势迅速崩盘,叛军乘势掩杀,唐军士卒尸横满地,兵马折损大半,好不容易敛集来的粮草辎重也尽数丢弃,万匹战马仅余三千,十万甲杖全失,尽为叛军所得,战后“安庆绪收子仪等营中粮,得六七万石”。
在此役中,史思明统五万兵马大破六十万唐军,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战后,郭子仪率部仓惶逃回洛阳,李光弼和其他八位节度使也各率残部溃归本镇。在溃逃路上,大唐败军把威风都宣泄在了老百姓头上,侵掠扰民,无恶不作,地方官吏无法制止,混乱的局势十多天后才结束。(“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在大溃败中,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所部军纪严明,能够“整勒部伍,全军以归”。其实在当时的唐军将帅中,以契丹人李光弼最为善战,治军也最为严明,他在整个安史之乱中也居功最大,远过名不副实的郭子仪,只不过身为异族,不似郭子仪般被后世中原史官大加吹捧,这才在声名上坠于郭子仪之下罢了。
在《新唐书》中,出于讳言失败、丑化叛军的动机,史官们竭力歪曲此次战败的事实,试图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激战时突然刮起大风,还说什么因为风大,所以“王师南溃,贼亦走,辎械满野”,可却无法解释,混战于一处的两军同时遇到大风,同时转身而逃,为何叛军在大风过后仍然强大,而唯有唐军分崩溃散,最终被史思明彻底击溃。笔者认为,在河南地界上,风级再大也有限,影响严重的区域决不会太大。唐军六十万人列开阵势,至少也要覆盖数十公里的区域,又有什么大风能选择性地将这六十万甲兵吹散,却独独对叛军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大风可没有私心,是不会像唐朝史官那样厚此薄彼地。
尽管此战的内情已经被削删得干干净净,但我们仅凭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便能够推测出大致的情况。在交战时大风突起,这事儿倒确实有可能发生过,但这最多只是一个溃败的加速器,绝不会是唐军战败的主因,将惨败的责任全都推脱给天气,不过只是史官们为了大唐遮羞,掩饰唐军的战斗力极度低下而作的诿过之词而已。六十万唐军看着吓人,其实不过是些纸老虎,这从其几个月连邺城这种小城都攻不下便可看出。这支由众多心思各异者仓促拼凑而成的庸碌之军,战斗力极低,士气也极差,于是当精锐的叛军铁骑突入阵中后,实与虎入羊群无异。而就在唐军还在苦苦支撑时,大风突起,纪律严整的叛军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快便能集结起来,再次发动攻势;而对于军纪涣散,本就已被打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的唐军来说,这场大风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郭子仪的后军率先扔下友军溃逃,各怀异心的各支唐军便纷纷抢着逃命,于是一场彻底的大溃败就此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