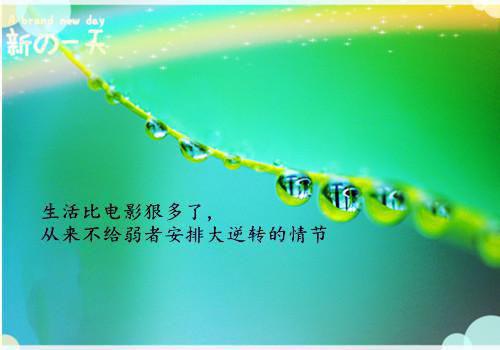时间,总是匆忙地不给人留一点余地,本来,几天前就想过在这个教师节写一点文字的,可是,不知不觉地一眨眼就到了9月10日,白天的忙碌根本无暇去写早已想写的只言片语,也只有在晚上敲下这不成敬意却又难以忘却的些许祝福。
说是祝福,其实是一些回忆,在我看来,回忆就是最好的纪念和祝福。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多年来,一双无奈而又沧桑的眼神总是时不时地袭击我内心,一直不曾停止,这倒不是因为我也从事过三两年的代课老师,而是其中有一位从事了20年的“代课老师”,因为1984年12月31日这个“一刀切”的日子,最终不得不黯然地离开他站了7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讲台,放弃“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之为“神圣”的职业。
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城市的街灯释放着昏黄慵懒的光晕,我从散发着烧烤味、弥漫着小贩噪杂声音的街道中走过,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国昌”,我抬头一看,是我初中时的老师。我惊讶地问道,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他带着淳朴的乡音和一贯的微笑说:“我在这里打工。”
我有些不相信地笑着说:“我不信,你是到兰州来办什么事吧。”
他笑着说:“真的。”
我一阵愕然。然后问道:“你不是还有转正的希望吗?”
他说:“没希望了。”
我无语,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把他带到就近的一家很小的的餐馆,要了几瓶啤酒,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边喝边聊。
我知道我的这位老师是非常开朗、乐观的,喜欢唱歌、歌声优美,也喜欢喝点小酒。我在老家时,每当孩子们散学、偶有闲暇,我们一起会猜拳喝酒。可是,那天晚上,因为当过兵,一向显得英姿飒爽,干练果断、精神焕发的他,脸上却写满些许的落寞和沧桑,而一贯地笑容也显得无奈,因此,我们没有划拳,只是碰杯。
也是那晚上,我知道了他是1986年从部队复原之后,通过县招聘进入家乡的学校任教,脱下武装换文装,走上神圣的讲台,对时年22岁的他来说,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和骄傲,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多么神圣的职业啊,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站就是20年。工资从最初的40元、到65元、再到后来的115元。这和当时体制内教师的千元乃至更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是,教师的职业和责任,使他从来没有以工资的多少而自我颓废或以薪水多少来付出自己的劳动,除了发工资时的心里落差之外,对孩子们的教学从不曾有丝毫的懈怠,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我来说,虽然他不曾给我带过主课,只上过音乐、体育课,但是,我知道他的敬业。
当时,家乡的学校属于村办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共有8个年级,他教过小学,也教过初中:无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还是音乐、体育等他都拿得起、放得下,特别是小学课程,他不但普通话标准,而且语文教学很出色。同时,他的大型文艺活动策划能力极强,1995年乡学区东部片区六一儿童节五校联欢庆祝活动、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活动、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五十周年活动等大型文艺活动,从策划筹备、节目排练到演出主持,他是全程指导完成者。
2000年前后,他的`爱人身体患病,既是每月65元的工资根本不够抓药,也没有动摇他做老师的信念。那时,一家四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但他仍为“老师”这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业默默坚守。直到2006年春节过后,考上师范学校的大女儿上学要学费,而举全家之力也无法打发孩子去学校时,这位有着军人坚强意志的男子汉再也撑不住了,从兄弟亲戚处举债送走女儿之后,面对一无所有的家庭、有病的爱人和国家政策对1984年后 “代课人员”的“一刀切”等种种厄境和行政政策的决绝,终于使他的思想崩溃、信仰坍塌,光荣神圣的职业根本无力解决现实的生活困境,所有的希望和追求化为乌有。为了家、为了妻儿,怀着复杂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站了7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讲台,收拾行囊外出打工,此时,他已43岁。
回想20年的时光,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的大好年华、还有对辛苦的妻子的亏欠及作为父亲责任的无能为力,面对劳累成疾的爱人、等钱上学的女儿,悲哀、无奈和辛酸淹没了一颗教书育人的希望之心,于是,奉献完大好年华之后,以“代课人员”的名义被“一刀”切断梦想,不得不在不惑之年告别妻儿,踏上打工之路。
面对一个将人生大好时光奉献给山村教育事业的恩师,我没有高尚和唯美的语言去赞美和歌颂,更写不出意境丰富的赞美诗,内心充满的是悲哀和凄凉,我所能做的只是安慰,安慰他全力以赴供养女儿毕业,去完成他没有走完的路,至少能弥补他内心些许的遗憾。
后来,我关注过“代课老师”或“代课人员”这个词,全国有几十万,他们曾被以“不合法、不合规(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正式认定和正式批准)的形式存在于校园里几十年,甚至目前还有,干着超负荷的工作,拿着体制内教师十分之一不到的薪水,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释放着自己的光和热,清贫的生活被高尚的职业安慰着无望的坚守。再后来,在媒体舆论的报道下,说有些地方出台政策给予补助,有一千多元的,也有伍佰元的,这算是给这些撑起山村教育的、“不合法”的“代课人员”的一点“牙祭”吧!
写到此处,时间已过了众人祝福的教师节,进入另一个日子,那些和我的恩师一样、曾经“不合法”的“代课人员”如今还顶着“老师”的称谓,是否还在搬砖、打混泥土、或在货运场装卸货物?亦或是在某个狭窄的出租屋里梦想他曾经的那三尺讲台?不得而知,但每年的9月10日,这个全国为教师高唱赞美诗的日子里,不知道曾得到他们授业的学子是否还记得曾经“不合规”的恩师?不知道我们的庙堂之上是否还想起他们?我亦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以“尊重教育工作人员”为宗旨的节日里,他们也是曾经其中的一员,哪怕他们“不合法、不合规”,但至少没有让偏远山村的教育拖了时代的后腿、拖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他们的“不合法、不合规”辜负的是家庭和妻儿,但没有“辜负”教师这个称号。所以,不要吝啬,请给他们在“教师节”也给予一点“廉价”的“祝福”,这不需要“割肉”。
《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村民不嫌其“不合法 ”而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们授业解惑,乡亲们不嫌其“不合规”称他们为老师,既使他们被“清退”,他们仍然是乡亲们眼中的老师,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了识字、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有了学上,此或许是乡亲们自己那个时代、连“不合规”的“代课人员”也没见过的“公知人员”口中的“愚昧”称谓吧。然而,这种“愚昧”的称谓,恰恰是乡亲们淳朴的尊师之道,因为“不合规”的“代课人员”的“不合法”存在不是乡亲们的错,也不是几十年拿着微薄薪水、干着牛马活的“代课人员”的错,他们失去的已经很多,不能再在这个节日里吝啬地连一句“祝福”也不敢说。
时间的脚步总是匆匆,历史的车轮昼夜不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些人老去或离开,有些人长大成熟步入社会,老去离开的人不是成为历史的丰碑,就是成为消散的云烟,然而,芸芸众生,任何人的转身或离开都影响不了自然的代谢和历史的进步。对于代课教师,对于一段三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史,乡村代课教师在这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中国的乡村教育无疑将是一部断层史,所以,中国的乡村教育史上,应该为他们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是日,仅以我人微言轻的文字,写下这被“忘却”的祝福,一个微不足道的公民姗姗来迟地祝福,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