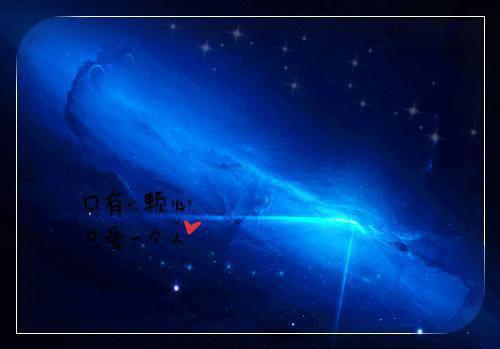“国画写生着重在各种形态之变化,构图之发生不已,确足医临摹徒穷纸上形似之病,济创造凭空结想之穷,为求国画新发展之道,若必专事写生,将吾国数千年来精神所寄之笔墨与气韵,一概废而不讲,则何以修养身心,提高品位?画其所重,亦郎世宁之流亚也,吾未敢从。”
这是吴茀之在《中国画理概论》“论写生”一节中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写生与笔墨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关系。此种以事写生,观形态,创构图,寄精神于笔墨、气韵,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贯穿其画迹之中。因而须探寻吴茀之的写生观与绘画理念之根源及其形成,以便更清晰地窥见他整体的艺术思想。
吴茀之二十世纪初出生于浦江县前吴村,自幼受家庭的文化氛围熏陶,受父兄、舅父诸长辈影响颇多,逐步形成对诗文、书画最初的审美情趣。吴茀之早年学步于家藏恽南田、蒋廷锡的花鸟写生册页,这对其后来形成关照自然的写生观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首先,以写生为革新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花鸟画多承袭海派画风,不脱“画谱气”,又受书画市场的影响,导致作品庸俗,没有生活的直接感受。茀之先生在《论写生》中指出:“欲全其形,欲新其境界,非从写生下手不可,由临摹到一些笔墨之经验与神韵上的领会以后,便当从事实地写作以明理境。久之,小则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之形态,大则于人生之意义,自然之变化,皆可了然于胸中,由此即景生情,即情造景,渐入创作而达到化境不难矣。”此可知其受恽南田“一洗时习,独开生面”写生思想影响之深。

其次,于具体写生的观察和运用中,茀之先生追求真实生动,意趣盎然,而后注以笔墨形质。他在《论写生》中则进一步阐述了恽正叔“极生动之致”的理法:“花卉的笔墨,常因气候而异。画春花,要得滋润含露之意,故宜用湿笔;画秋冬之花,要得其傲霜之态,故以燥笔为之。凡画花卉,要得其迎风,带雨含露之意态。”再则,茀之先生又长于诗文,尚情趣,作品中洋溢着很强的抒情性。《南田画跋》亦记:“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慑情,不可使鉴者不生情。”可见,吴茀之写生理念上直接继承恽氏遗风,然于技法层面则更倾向于水墨写意一路,主性灵,重格调。
茀之先生在去上海求学之前,主要是在舅父、长兄指引下学习书画。舅父黄尚庆书法师颜鲁公笔意,以文衡山体势运之,形成了点画沉厚,书写秀逸之风格;水墨画有扬州八怪之遗风,笔墨酣畅,近黄瘿瓢,喜写荷花、芦蟹等农家题材。兄长吴士维师于舅父,画风相似,晚近边寿民。前辈的熏陶,耳濡目染,使吴茀之较早地对以清代石涛为渊源的扬州画派为主导的中国画革新精神有了最初的了解。
1922年,吴茀之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成了中国近代学院美术教育最早的科班学生,期间受业于诸闻韵、许醉侯、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经亨颐等,而得到诸闻韵直接教诲最多。闻韵先生是吴昌硕的家庭教师,师法缶翁,但已初具面貌,对吴茀之形成个人面貌产生了引导作用。当时国民政府每况愈下,爱国人士多方取经,救国救民。文化界以蔡元培、经亨颐、徐悲鸿、刘海粟等为代表以美育教化人,重振民族之精神,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这一时期画风多法缶翁大写意,强以气势。近而上追清代李复堂。复堂早随蒋廷锡习画,在蒋氏和南田之间,后师高其佩,形成了重视生活,率意挥写,崎岖淋漓的画风。期间还旁涉青藤白阳、石涛、八大、扬州画派、任伯年、厉良玉、赵之谦、蒲华等诸家之长。这些都与茀之先生早期绘画思维不谋而合,之后,茀之先生艺术创造上多以此为动力,为以绘画表现时代、人格精神的观念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2年夏,吴茀之与诸闻韵、潘天寿、张书旗、张振铎5人在上海发起了白社国画研究会。时年33岁的吴茀之任上海美专教授,在对师友、古人等多方取法之后,已基本确立了以“扬州画派”的革新思想为主的绘画理念、审美以及自己大致的取法方向,直到其晚年作品,我们已看到他的画风渐入佳境,呈现出醇厚平和之气。然而因“文革”摧残,终未能遂其毕生所愿,实在不能不令人怅然。
笔者认为,在中国书画艺术生生不息的发展长河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个体特质的展现与传统文化品格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