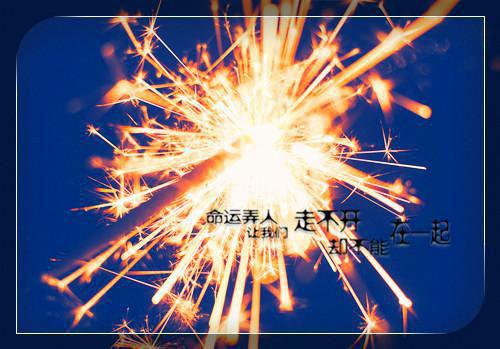早年
1889年6月11日(旧历)安娜出生在黑海沿岸敖德萨近郊的“大喷泉”。父亲是一名退役海军工程师。当安娜决定要写诗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不“辱没”父亲的姓氏她选择了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正是这个姓氏响彻俄罗斯整个文坛,而非“戈连科”。
安娜六岁时父母离异,这给她的童年遮上了一层阴影。她的无忧无虑的年华是在美丽的皇村度过的。她最初的回忆献给了皇村:“富丽堂皇、翠绿欲滴的花园,奶妈带着我去玩耍的牧场,杂色的马驹驰骋的赛马场,年代久远的火车站…”彼得堡(后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与她的一生紧密相连,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成为一名诗人,列宁格勒是我的诗歌的空气。”在这里她度过了16年。童年的生活环境给了安娜无穷的创作源泉。从小她便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第一首长诗《在海边》描写了自己的童年。
婚姻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结束了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恋爱。然而婚姻只是走向不幸的开始。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我们俩作未婚夫妻的时间太长了,我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结婚时,他的激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婚后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玛托娃一头扎入了诗歌的创作中。
古米廖夫早期诗歌中有不少是描写安娜的,她时而是美人鱼,时而是魔法师,时而是凡间女子,时而是天上月亮。这条美人鱼具有难以名状的幽怨气质,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诗歌。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在诗坛引起不小反响。1914年《念珠》出版,读者抢购一空,争相传诵。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以清新委婉的笔触给当时象征主义为主宰诗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打破了当时晦涩的象征气氛。

苦难
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至于离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两位诗人都向往自由,追求创作灵感。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从古米廖夫一方来说,他不愿屈从于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严。他认为,两个诗人的结合是荒谬的。所以作为两位当时的著名的诗人他们认为分手是最好的选择。就此两位诗人分道扬镳,各自重新组合家庭,然而他们的第二次婚姻又是不幸的。他们在诗人与幸福之间选择都选择了作诗人,放弃了个人的幸福。
在阿赫玛托娃的爱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鲍﹒安列坡。阿赫玛托娃的诗集《白鸟集》和《车前草》又大部分诗是献给安列坡的。如果说《黄昏》和《念珠》里没有美满的爱情,充满了悲凉,那《白鸟集》和《车前草》里则激荡着感情的洪流,这是关于“王子”复活的话题..然而这份感情是没有结果的相思花。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身为白军军官的安列坡被迫逃往英国。同时也有不少诗人、作家因不了解革命而远走异国他乡。对于当时的移民倾向阿赫玛托娃表示“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Не с теми я,кто бросил землю\на растерзание врагам”,并有好几首诗表示坚决反对,尽管她当时也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但她没有逃避,也没有后退。她寄予这片生她养她的故土以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诗人,她的诗充满了公民感,正如涅克拉索夫所说:“你可以不作一名诗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阿赫玛托娃斥责当时的侨民为Отступник,изгнанник,пленник чужой,странник等等,认为“外国的面包充满苦艾味”,同时她相信祖国一定会走出混乱,走向复兴:“Пускай на нас еще лежит вина,---\Все искупить и все сиправить можно.”
尽管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安排一条风顺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她的诗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1924年因《耶稣纪元》中的一些诗篇激怒了当时的政府官员,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禁,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无疑也是被判死刑。然而她没有一蹶不振,没有销声匿迹,在这段“沉默”的时期内她研究了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创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诗歌,普希金给了她无穷的创作灵感和人生启迪。
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阿赫玛托娃身居塔什干仍不忘尽快获得列宁格勒的消息,在大围困的艰难时期她与她的人民同在,她以自己的诗歌激励人民,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
卫国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再次遭到不幸。1946年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作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严厉批判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认为“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дело далё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оно чуждо совр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рпимо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наших журналов.”就这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她本人也被指责为“半修女、半淫妇”,被苏联作协除名,直到1952年一切才得以平反。
日丹诺夫给文学扣上政治的帽子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最主要的是他没有透过阿赫玛托娃描写的不幸生活的表面看到个人的悲剧其实是由时代的悲剧造成的,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将生活提炼为艺术,而她的艺术方法是独特的,虽然阿赫玛托娃写不出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但她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角度观察并写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回荡着时代的强音。
1962年阿赫玛托娃完成自传体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历时22年,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晚年,荣誉纷至沓来,1964年阿赫玛托娃在意大利接受了“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诗人的艺术得到世界的认可。1966年3月这位饱经风霜的女诗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结束了她77年的坎坷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