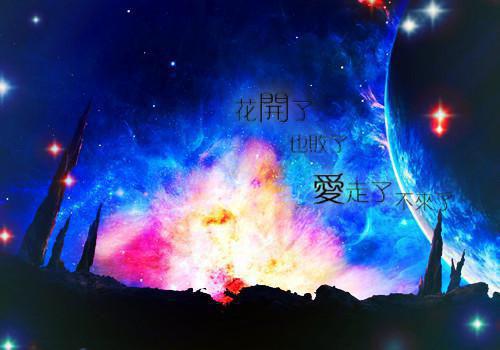1975年,一个皮包骨头的老太太走出了秦城监狱。
她被直接送上火车,一列火车又换了一列火车,之后再换汽车,最终,她回到了大治——湖北东南一个小城。
那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前来迎接她的亲人们惊呆了,他们见到了这样一个老太太。

他们无法把眼前这个两眼凹陷的老太和家里相片簿上的那张照片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上,这个老太太是长这样的:
这时,扣在她头上的帽子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劳改释放犯……
这一辈子,她坐了四次牢,两次在解放前,两次在解放后。耐人寻味的是,前两次坐牢,是因为被怀疑为共产党;后两次坐牢,则因为被认为不是共产党。
她叫黄慕兰,一个红色女特工——尽管她很讨厌被人叫作“美女特工”之类的称号。
2017年2月7日中午,她去世了,110岁。
黄慕兰的一生,当然是一个传奇。
但这传奇,也许并不如她所愿。
一
她其实有着比许多人都幸运的童年。
因为有一个开明的父亲,她没有缠足,从小接受教育,作诗写字。“五四”运动之后,12岁的她第一批进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在中共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
丁玲
向警予
杨开慧
蔡畅
……
看了上述名字,我们可以知道,黄慕兰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女性。
虽然出嫁时有“一车厢的嫁妆”,然而她的丈夫——那位比她大四岁的世家子弟丈夫整天沉醉于鸦片中,偶尔还以打丫鬟出气。黄慕兰偷偷给前来看她的父亲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说她过不下去了,要求回家。没想到,父亲居然同意了她的要求,让舅舅把她接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和婆家联系。
黄慕兰惊讶于父亲的通融,很久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秋瑾的粉丝。
沿着前辈秋瑾的路,黄慕兰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在北伐前夕前往汉口,她投身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那时候,国共仍在合作,黄慕兰不知道,她将面临人生的一道选择题。
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曾经让她去莫斯科学习,然而,瞿秋白来找她,希望她服从党的安排,不要去。
于是,她没有去,“要是去了,就和蒋经国是同学。”
“服从党的安排”,这将成为她一生的关键词。
当然,不去大约还有另一个原因,她恋爱了。1927年,20岁的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和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宛希俨结婚。
结婚没有举办任何仪式,董必武在会上宣布了一下,报纸上刊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黄慕兰对这个启事非常看重,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和第一任丈夫离婚。
和宛希俨结婚之后,黄慕兰开始了地下党工作。她跟着丈夫前往江西,负责情报的联络和中转。在那之前,只在传说里存在的“列宁用牛奶写密码”的故事,被黄慕兰真实体验了,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需要掌握浓淡尺度的米汤水,密码有时被写在《圣经》里,在小旅馆里,联络员们以暗号接头。
这种“潜伏”生活,黄慕兰显然是紧张而兴奋的,更为难得的是,她还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少年时的革命梦想,在女儿身上实现了——毕竟,黄爸爸当年还有一个好基友,叫谭嗣同。
过了一年,黄慕兰生了一个儿子。
宛希俨都来不及看看儿子的样子,就被派往赣西南,四个月之后,他牺牲了,年仅26岁。
很久之后,黄慕兰才得到了这个消息,告诉她这则消息的是饶漱石。请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在黄慕兰之后的人生里,这个名字还将出现多次。
这是黄慕兰第一次与亲人的死别。
这样的死别,不是最后一次。
二
1928年12月,她再次听从组织安排,到上海担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在临行前,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刚刚断奶的儿子被送到了宛希俨的父母家。
没想到,刚到上海不久,黄慕兰就跳了黄浦江。
跳江的理由有点不可思议。
在上海,黄慕兰遇到了武汉时的老相识贺昌,贺昌当时已经升任中央委员,听了黄慕兰的遭遇,贺昌便经常劝慰她,两人之间,渐渐有了感情。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她的第一想法是,要征求组织同意。
组织同意了,但因为贺昌的身份,组织上要求她隐瞒结婚经历,对外只说自己是宛希俨的遗孀,到上海来找工作。
有一个人炸裂了,这就是之前一直对黄慕兰展开追求的饶漱石,从江西到上海,饶和黄慕兰在一起工作了很久却没有获得佳人芳心。于是,他有点阴阳怪气对黄慕兰说:
哟,原来攀高枝去了!
这句话戳中了黄慕兰,她觉得受到了莫大侮辱,在极端刺激下,她把一本会议纪要本丢在了黄包车上。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向组织交代,头一昏,脑一热,黄慕兰跳江了。
第二天的上海小报上,出现了一条“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新闻。这是被救起的黄慕兰对警察撒的谎。
后来,她对前来采访的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承认,那时候,她曾经想过,是不是要回家。但她已经回不去了,她的母亲告诉她,第一任丈夫认为他们的婚约还在,曾经去她家里找过她。
不能回家,只能继续工作。周恩来派人领回了黄慕兰,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她再次开始了自己的女革命者工作。可以说,为了这份工作,她献出了自己所有,1929年,因为组织工人运动,身怀有孕的黄慕兰被关进监狱,她拒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她一直津津乐道的,却是在监狱里,她在狱中难友彭湃的领导安排下,成立了一个党支部。
100天之后,黄慕兰出狱了,不久生下了孩子。孩子没有姓黄,也没有姓贺,取名卢小平——这是贺昌的主意,他没有经过黄慕兰同意,就把那个孩子送给了自己的同事卢彪,他的理由是:
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将来他长大了,也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
这是黄慕兰第二次和孩子分别。这个孩子,一直到解放后,才和黄慕兰相认。
因为受到李立三的牵连,贺昌被降职“靠边站”,急于立功的贺昌希望前往苏区打游击,戴罪立功。他把报告打上去,依然没有告诉黄慕兰,然而,敏感的黄慕兰还是感受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因为那几天,“他对我特别体贴”。
当得知贺昌决定前往苏区的消息后,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她坚决不愿意服从分配。她已经失去了一个丈夫,这一次,如果不和丈夫一起去,她很清楚,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贺昌对她说,她的这种想法是“资产阶级的爱”,而“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很快,组织上也下了决定,不同意她和贺昌一起去,理由是,去苏区一路都是农村和山区,她的“皮肤太白”,很容易识破。
现在看来,另一个显然是,组织上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她。“皮肤太白”的她在苏区毫无用处,甚至有可能拖贺昌的后腿,而留在上海,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美貌、谈吐与教养,继续做地下工作。
她那么像一个大家闺秀,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大家闺秀,以“名媛”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更为方便。更何况,她的身边当时还出现了一位沪上鼎鼎有名的大律师陈志皋。
三
陈志皋对她颇有好感,陈志皋的父亲特别喜欢黄慕兰,还认她为干女儿,两人刚刚相识,陈志皋的父亲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她营救出了被捕的中央候补委员关向应。
△陈志皋
黄慕兰的自传里,在认识陈志皋之后,她委实做了好几件大事,和营救关向应比起来,“第一时间通报向忠发的叛变”和“化解周恩来脱党传闻”这两件事,更值得一提。
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忽然偶遇了一个叫曹炳生的人,他是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和陈志皋是同学。
闲聊中,曹炳生聊起了一条“大新闻”,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口音很重,“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黄慕兰把听来的这个消息通知了潘汉年,潘汉年立刻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总书记向忠发,于是及时告知党组织,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及时转移,避免了党组织的破坏。
而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月之后,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由于向忠发、顾顺章等领导人的接连叛变,这则启事在当时也迷惑了不少人。于是,组织要求黄慕兰再次出马,通过陈志皋,找到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登了这样一则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这则启事确实很妙,既洗清了周恩来脱党的罪名,又保护了律师,正如黄慕兰晚年所说的:“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这两件事,在黄慕兰的自传问世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尤为激烈,并要求出版社收回自传。看来看去,质疑的论点无非是:这是党组织的精心运作的结果,而媒体却把重心放在了一个女人的个人功劳上,“造成一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生死系于一个女子一颦一笑之间的误导,这样做已经歪曲了历史,损害了共产党及我党领导人的形象。”(澎湃网对吴持生的采访)
黄慕兰的口述也许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有两点是不可辩驳的。第一,无论是不是组织的安排,营救关向应、通知潘汉年以及刊登澄清启事的直接执行者,都是黄慕兰。
第二,黄慕兰确实是为了党组织,和陈志皋展开交往,也许组织一开始没想到他们会谈恋爱,但组织并没看不出,陈志皋对黄慕兰的爱意。因为陈志皋有一次来看黄慕兰时,贺昌还在家里,只好躲在卫生间,听见陈志皋对黄慕兰说:“你又抽烟了,抽烟对身体不好。”贺昌没有任何的不满,而是非常高兴地询问陈志皋能否救出关向应。
和许多谍战故事一样,陈志皋爱上了黄慕兰,并在1933年向她求婚了。
而这个故事,同样疑团重重。
黄慕兰的口述里,在两年里,陈志皋向她求爱数次,但她都拒绝了,因为惦记杳无音讯的贺昌,她用“门不当户不对”这个理由拒绝了陈。但陈居然“咬破手指”,给她写了血书。黄慕兰再次向组织汇报了情况,最后,她根据组织要求,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求婚。
而在反对者看来,黄慕兰当时和陈志皋结婚,完全是不顾组织原则的个人行为,并没有获得组织同意。所以,在和陈结婚之后,组织对她做出了“淡化脱党”的处理。
△陈志皋和黄慕兰的结婚照
事实已经如迷雾一般难以认清,但同样有一点不可否认,在婚后,改名黄定慧的黄慕兰并没有停止为党工作。
她曾经多次资助当时的进步社会活动,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过自己跟着许广平去向“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筹借款项。根据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的说法,她甚至帮助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他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
她也曾经遇到家庭危机,陈志皋重逢了自己的初恋,不断有人告诉她,陈志皋和初恋“旧情复燃”了。这时候,她只有一个想法,去延安。打了无数次报告,均不被批准。1942年,黄慕兰到重庆见了周恩来夫妇,再次表达要求离开陈志皋前往延安。周恩来劝她不要离开陈志皋,“不要瞎吃醋”。不久,因为“胡蝶行李被盗”事件,黄慕兰再次被捕。在狱中,军统反复盘问她与共产党的关系,然而一无所获。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她说:
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
两年之后,黄慕兰被保释出狱。而这时,她还不知道,早在1935年,贺昌在江西打游击战时,遭到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终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贺昌遗像
四
1949年,上海解放。黄慕兰夫妇将迎来最令人瞠目的一刻,已经成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告诉黄慕兰,她的党组织关系不会被承认。她的老上司刘少文推荐黄氏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被否决。
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他觉得黄慕兰的党员身份不被承认,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陈志皋对她说:“要是1942年的整风再来一次,你还能忍受吗?”“我能。”黄慕兰让丈夫先走,而她带着四个孩子留下,她始终相信组织会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她已经为了组织,牺牲了太多太多。
△陈志皋和黄慕兰以及他们的孩子
她没能等到陈志皋,他们再也没有见面,陈志皋后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去世。1953年,她不得不写信单方面跟陈志皋离婚。两年后,因为受到“潘扬案”牵连,黄慕兰锒铛入狱,刚刚被放出来,又遇上了“文革”。
在文革中,她因为箱子里留着一件陈志皋的长袍,就被红卫兵强行剃光头:
你嫁到这样的人家,还能是中共党员吗?你不是叛徒还能是什么?还有脸不服判决上诉,对你这种人不加重处罚行吗?
她每天要负责打扫六栋楼的卫生,并且不停检查,写交代材料,因为写了一句“永不消沉”,就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鞭打,皮带上的钢扣打断了她的三根肋骨。
所以,当她被关进秦城监狱时,居然庆幸,觉得监狱比在外面受批斗好太多太多。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黄慕兰走出秦城的那一天开始,她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一个——申诉。
而她的申诉要求,也只有一个,要求组织承认她的党龄。许多人都劝她,既然已经落实政策,不要纠结,她和贺昌所生的儿子贺平对她说:“妈,当年您如随同爸爸去了苏区,说不定早已和爸爸一同牺牲了。还是现在这样更好,我们都长大成人,你应该过上好日子了。”但黄慕兰想的是:
如果我去了苏区,我现在就是一个烈士了。
1991年,她最终获得承认连续的党龄。
对于外界对她的质疑,黄慕兰始终不发一言,据说,她写了好几个版本的口述回忆录,最详细的版本她没有公布,因为是准备交给党组织的,不能够对外公开,这是组织纪律。
要服从组织安排,瞿秋白对她说的那句话,她真的记了一辈子。
只有一次,她对来找她做口述史的王政第二次讲起自己的故事,她忽然反复说起她的第一任丈夫,说起那个大她四岁的世家子弟,说起她塞给父亲的那张要求回家的小纸条,她说:
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现在,她的故事真的结束了。